孩子们的血液工厂。 3的一部分

红海岸营地的大多数孩子都没有长时间逗留:他们的血液在西方需要。 在有盖帆布机中,他们被送到其他营地。 最接近的是Salaspils。 这个集中营是纳粹在1941年在拉脱维亚境内创建的。 来自白俄罗斯,普斯科夫和列宁格勒地区的儿童在惩罚行动中被捕,被带到这里。
官方名称是Salaspils扩大警察监狱和劳动教育营地。 纳粹在他们的医学实验中使用了少年囚犯。 在Salaspils营地的三年期间,超过3,5千升儿童的血液被抽出。 青少年囚犯常常成为“完全捐助者”。 这意味着他们从血液中取血直到死亡。 尸体在火葬场窑中被摧毁或倾倒入利用坑。 在其中一个人中,一名德国女子意外地发现了Zina Kazakevich,一个几乎没有呼吸的白俄罗斯女孩:经过另一次采血后,她睡着了。 她被认为死了。 她已经在一个富有同情心的德国人的房子里醒来了:frau经过了利用坑,发现了一声骚动,掏出一个女孩离开了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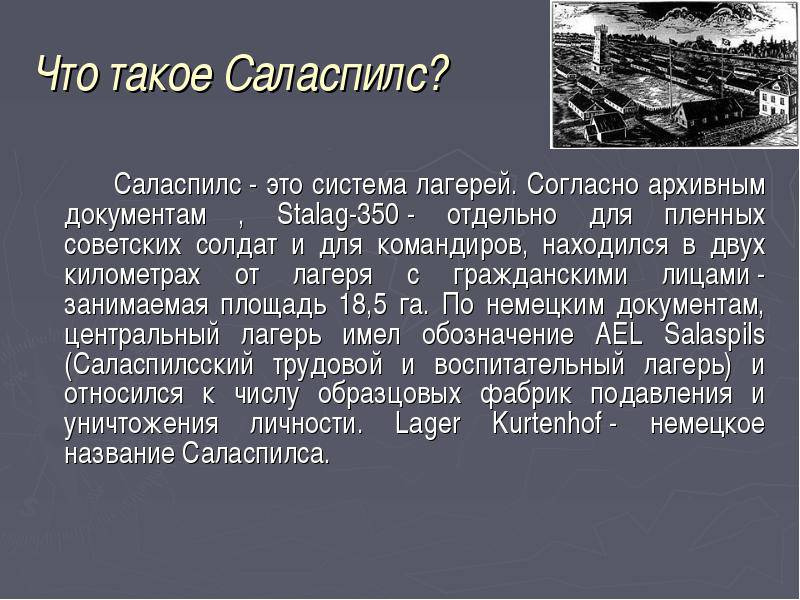
Matsulevich Nina Antonovna回忆道:“战争开始时,我已经六岁了。 我们很快就成熟了。 在我眼前 - 一些摩托车,机枪手。 它变得吓人了,我们立刻跑到我母亲的小屋里。 我们试图逃离警方突袭,妈妈把我们藏在一个蔬菜坑里。 晚上我们离开了。 我们在麦田里徘徊很长一段时间,希望找到至少一个我认识的人。 没有人认为战争会如此漫长。 德国人在森林里找到了我们。 他们用狗袭击我们,推开机枪,带我们上路,带我们到火车站。 热火。 我想吃。 我想喝。 都累了。 到了晚上,火车到了,我们都挤进车里。 没有厕所。 只有在汽车的右侧才有一些小孔被切掉。
我们无休止地开车。 所以在我看来。 作文一直停止。 最后,我们被告知要离开。 在Daugavpils市的营地被抓住了。 他们把我们放在相机里。 他们不时地从那里抢走并带回了十七岁的女孩,她们被暴力殴打,受伤,精疲力竭。 他们把它们扔在地板上,不允许任何人接近。
我们的妹妹托尼亚在那里去世了。 我不记得已经过了多少时间 - 一个月,一个星期。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再次被带到监狱院子里并开车进去。
我们被带到Salaspils营地。 德国人非正式地将其称为“血液工厂”。 正式 - 教育和劳动力。 所以德国人在他们的文件中将他命名为他。
但是,当有三个孩子甚至是婴儿期时,我们可以谈论什么样的儿童劳动教育!

我们在脖子上得到了令牌;从那一刻起,我们不再有权给出我们的名字。 只有数字。 我们没有在军营呆很长时间。 我们建在广场上。 他们通过标签识别并带走了我的两个姐妹,带走了它们并带走了它们。 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在广场上再次建造我们,并根据数字再次带走了我的妈妈。 我们一个人待着。 当他们带走我的妈妈时,她不能去。 她被武器带领。 然后他们抓住她的胳膊和腿,松开并扔进了身体。 也和其他人一起完成。
他们让我们出去散步。 当然,我想哭和尖叫。 但我们不允许这样做。 我们仍然坚持我们所知道的:我们军营后面有军营,战俘是我们的士兵。 我们会悄悄地背弃他们,但他们却默默地对我们说:“伙计们,你们是苏联儿童,要有耐心,不要吝啬。 不要以为我们被遗弃在这里。 我们很快就会发布。 相信我们的胜利。“
我们心中记录着我们不应该哭泣和呻吟。
今天我有一个来自萨拉托夫学校的女孩№23给了我这首诗:
一个七岁女孩的眼睛,
像两个褪色的灯。
在孩子的脸上更加引人注目
大而沉重的忧郁。
她沉默,你不会问她,
和她一起开玩笑 - 作为回应的沉默,
好像她不是七,不是八,
还有很多很多苦涩的岁月。
当我读这首诗时,我哭了半天,我无法停止。 就好像这个现代女孩沉入洞里一样,为没有父母的孩子们撕下来,饥肠辘辘而生存下去是什么感觉。

最糟糕的是,当德国人进入营房并在桌子上摆放他们的白色工具时。 我们每个人都摆在桌面上,我们自愿伸出一只手。 那些试图抵制,捆绑的人。 喊叫没用。 因此,他们为德国士兵从儿童身上抽血。 来自500克以及更多。
如果孩子无法到达,他们就带着他并且已经无情地带走了所有的血液并立即将他带出了门。 最有可能的是,他被扔进了坑或火葬场。 白天和黑夜都是臭,黑烟。 烧毁了尸体。
战争结束后,我们在那里进行短途旅行,似乎地球仍在呻吟。
早晨,一位拉脱维亚女护士长着一顶戴着帽子的高个子金发女郎穿着长靴,带着鞭子进来。 她用拉脱维亚语喊道:“你想要什么? 黑色或白色的面包?“如果孩子说他想要白面包,他就被扯掉药物 - 监狱长用这条鞭子打他,直到她失去意识。
然后我们被带到尤尔马拉。 那里有点容易。 虽然有床。 食物几乎一样。 我们被带到了餐厅。 我们立刻引起了注意。 在我们读到“我们的父亲”的祷告之前,我们没有权利坐下来,直到我们希望希特勒健康和他的快速胜利。 我们常常遇到过。
每个孩子都有溃疡;如果你划伤,血液就会消失。 有时男孩们设法得盐。 他们把它给了我们,我们小心翼翼地用两根手指,小心地挤了这些珍贵的白色种子,这种盐开始擦这个疼痛。 你没有pikesh,不要呻吟。 老师突然接近了。 这将是一个紧急情况 - 他们拿盐。 调查将开始。 挨打,被杀。

在1944中,我们被释放了。 3七月。 我记得这一天。 我们的老师 - 她是最好的,用俄语讲话 - 说:“做好准备,跑到门口,tip脚,这样就不会有沙沙声”。 她带我们晚上在黑暗中带到了防空洞。 当我们从防空洞中解救出来时,每个人都喊着“华友世纪”。 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士兵。
我们开始学习在报纸上写下“a”字母。 当战争结束时,我们被转移到另一个孤儿院。 我们得到了一个带床的花园。 在这里,我们开始以人性化的方式生活。
我们开始拍照,找出有人出生的地方。 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只有名字 - 科罗廖夫村。
一旦我们听说德国投降了。
我们的士兵在武器下举起,像球一样摔倒。 他们和我们哭了,这一天给了我们很多生命。
我们得到了论文:我们被分配到第一类受害者。 在括号中指出 - “医学实验”。 我们不知道德国医生对我们做了什么。 也许注射了一些药物 -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还活着。 我们的医生想知道我是如何完全没有甲状腺的。 我输了。 她就像一个线索。
但我无法确切地知道我出生的地方。 我认识的两个女孩是从孤儿院带走的。 我坐着哭了。 女孩的母亲看了我很久,想起她认识我的母亲和父亲。 她在一小块地方写下我的地址。 我用拳头敲了敲老师的门,然后踢了出去:“看看我出生的地方。”
然后我被说服冷静下来。 两周后,答案来了 - 没有人活着。 祸患和眼泪。
我的母亲被发现了。 事实证明,她被劫持到了德国。 我们开始聚集在一起。
我记得我在一切细节上与母亲见面。
不知怎的看着窗外。 我看到一个女人在走路。 晒黑了。 我喊道:“妈妈来找某人。 今天将被带走。“ 但出于某种原因,我感到震惊。 我们房间的门打开了,我们老师的儿子进来说:“妮娜,去吧,他们在那里缝了一件衣服”。
我进入并看到靠近墙壁,一名妇女坐在靠近门的小凳子上。 我路过。 我去找那个站在房间中间的老师走近她,按下了自己。 她问道:“你认识这个女人吗?”我回答:“不。”
“Ninochka,女儿,我是你的母亲,”妈妈无法抗拒。
我的双腿被拒绝了,就像棉花,木头一样。 他们不听我的话,我不能动。 我向老师施压,我按,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幸福。
“Ninochka,女儿,来找我,”母亲再次打来电话。
然后老师把我带到了我的母亲,让我并排。 妈妈拥抱,吻我,问道。 我告诉她住在我们旁边的兄弟姐妹,邻居的名字。 所以我们终于确信他们的关系。
我的母亲带我离开孤儿院,我们去了白俄罗斯的家乡。 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 在我们村的郊区谈话。 脱粒谷物。 因此,德国人聚集了所有留下来并且没有像我们一样逃跑的居民。 毕竟,人们认为战争不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们在芬兰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幸存下来,德国人没有对他们采取任何行动。 他们只是不知道德国人已经完全不同了。 他们所有居民都把他们赶到了现在,用汽油浇灌。 那些从火焰喷射器中幸存下来的人被活活烧死了。 有些人在广场上被枪杀,迫使人们提前挖洞。 所以我的叔叔失去了他的全家:他的妻子和四个孩子在他家里被活活烧死。
我们住在这里。 我有孙女。 我想祝大家幸福和健康,也要学会爱你的祖国。 如下。
纳粹焚烧了档案馆,但那些用自己的眼睛看到暴行的人仍然活着。 营地中的另一名囚犯Faina Augostane回忆道:“当我们全部分布在军营中时,他们开始从孩子身上取血。 当你走在迷雾中,你不知道你是否会回来时,这是可怕的。 我看到一个女孩躺在过道上,她的腿上有一片皮肤。 流着血,她呻吟道。“ Faina Augustone对当前拉脱维亚当局的官方立场感到愤怒,他们声称这里有一个教育和劳改营。 “这是一种耻辱,”她说。 “他们从孩子身上取血,孩子们死了,堆成一堆堆。” 我失去了我的弟弟。 我看到他还在爬行,然后在二楼他被绑在一张桌子上。 他的头垂在了一边。 我打电话给他:“Gene,Gene。” 然后他从那个地方消失了。 他被当作一个原木扔进了一个坟墓,里面满是死去的孩子。“
劳改营 - 这是纳粹文件中关于这个可怕地方的正式名称。 那些今天重复这一点的人重复了纳粹 - 希特勒的用语。
拉脱维亚在1944解放后,立即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法令设立了调查德国法西斯侵略者暴行的特别国家委员会。 在今年5月的1945中,在审查了死亡营地(54坟墓)的五分之一领土之后,该委员会发现632是一名5至10岁儿童的尸体。 尸体被分层排列。 总而言之,在心室中,苏联医生发现冷杉球果和树皮,可见饥饿的迹象。 有些孩子发现注射了砷。
这些年的新闻报道公正地展示了雪下的一堆小尸体。 活埋的成年人站在他们的坟墓里。
在发掘过程中,他们发现了一幅可怕的照片,其照片被一代以上的人震惊,并被命名为“Salaspils Madonna” - 埋葬的母亲,将婴儿压在胸前,活着。
在营地里有30军营,最大的一个是孩子们的营房。
紧急委员会发现,7 000儿童在这里受到折磨,只有100 000人死亡,比布痕瓦尔德更多。
从1943开始,发生了几次惩罚行动,之后营地充满了囚犯。 拉脱维亚惩罚性警察营在德国难民营服役。
而不是识别黑页 故事拉脱维亚开始在欧盟担任总统,禁止在2015举办一场纪念Salaspils受害者的展览。 拉脱维亚官方当局以一种相当奇怪的方式解释了他们的行为:该展览据称损害了该国的形象。
目标很明确:首先,拉脱维亚民族主义者试图粉饰自己,因为他们在人类种族灭绝中的作用非常大。 红军总情报局报告说:“在入侵党派地区期间被囚禁的人口部分被劫持到德国,其余的则在拉脱维亚出售给土地所有者的两张邮票。”
其次,西方国家现在希望将俄罗斯从胜利的国家和世界的解放者从纳粹主义转变为纳粹主义的盟友。 尽管如此,“偷来的童年”展览在巴黎的俄罗斯文化中心开幕。
然而,拉脱维亚官员仍然认为这个阵营无法与布痕瓦尔德相提并论。
悲惨的目击者安娜·帕夫洛娃(Anna Pavlova)已经了解到这一点,他说:“上帝禁止对这些官员进行测试,他们声称相反。 不要让战斗体验儿童和女孩遭受的痛苦,为此德国人特别挑出了一个单独的小屋,并为了舒适而发动士兵。 那里的尖叫声太可怕了。“ 上帝保佑!
信息